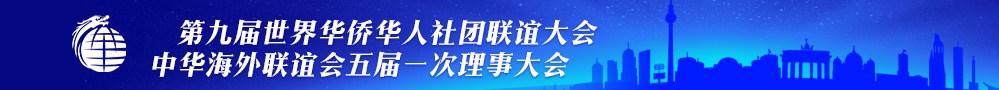本文图片均为上海自然博物馆老馆
摄影:陆洁

 二楼的古生物大厅,硕大的合川马门溪龙骨骼矗立在那里。记得儿时来参观时,大厅顶部的光线透过明亮的彩色玻璃一泻而下,大龙似乎面朝观众缓缓走来,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在此展厅中,只需要轻轻移动脚步,便可以从寒武纪到奥陶纪,从侏罗纪到白垩纪,生物千万亿年漫长的演化只在咫尺之间纳入眼帘。无脊椎动物展区,腔肠动物和节肢动物慢慢地演化,有些被浸泡在福尔马林的液体中,优雅而安静,一个个手工制作的景箱细致入微地展示了生物的形态特点和生活环境。越来越深入其中,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动物分门别类,鸟类展区是我儿时最喜欢的部分,形态各异的鸟那不同的眼神凝视着观众,并也展示着物种的多样性,生物的演化从陆地往空中发展……
二楼的古生物大厅,硕大的合川马门溪龙骨骼矗立在那里。记得儿时来参观时,大厅顶部的光线透过明亮的彩色玻璃一泻而下,大龙似乎面朝观众缓缓走来,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在此展厅中,只需要轻轻移动脚步,便可以从寒武纪到奥陶纪,从侏罗纪到白垩纪,生物千万亿年漫长的演化只在咫尺之间纳入眼帘。无脊椎动物展区,腔肠动物和节肢动物慢慢地演化,有些被浸泡在福尔马林的液体中,优雅而安静,一个个手工制作的景箱细致入微地展示了生物的形态特点和生活环境。越来越深入其中,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动物分门别类,鸟类展区是我儿时最喜欢的部分,形态各异的鸟那不同的眼神凝视着观众,并也展示着物种的多样性,生物的演化从陆地往空中发展…… 整个老馆的建筑与馆内陈设形成了默契和充满魅力的美感,一方面我被这种神秘而诗意的美感所打动,另一方面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整个场馆的布局和陈设也和这些美感融合在一起,混杂了福尔马林气味刺激着我的鼻腔和大脑。如古人类厅是按照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将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意识形态纳入其中。生物的分类按照从低等到高等,有害和有利,与人类生产实践关系的实用主义来区别和划分,展厅中以极端认真的态度手工书写的美术字体中也时时处处地体现了这点。这些略显瘦长而遒劲有力的文字带有装饰性的美感,也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我们能感受到所有这些都隐藏在文字背后,默默地控制着整个老馆,与世隔绝并逐步消失。
整个老馆的建筑与馆内陈设形成了默契和充满魅力的美感,一方面我被这种神秘而诗意的美感所打动,另一方面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整个场馆的布局和陈设也和这些美感融合在一起,混杂了福尔马林气味刺激着我的鼻腔和大脑。如古人类厅是按照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将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意识形态纳入其中。生物的分类按照从低等到高等,有害和有利,与人类生产实践关系的实用主义来区别和划分,展厅中以极端认真的态度手工书写的美术字体中也时时处处地体现了这点。这些略显瘦长而遒劲有力的文字带有装饰性的美感,也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我们能感受到所有这些都隐藏在文字背后,默默地控制着整个老馆,与世隔绝并逐步消失。 项目有一部五十分钟的实验影片,这是我与吴建新导演第一次的合作。影片以老馆的搬迁作为背景,从摄影师的视角把标本制作的过程、摄影师个人对幼年时光的回忆联系在一起,追求幻境和现实之间某种漂浮感的意境。我希望通过影片展示摄影师的个人身份、记忆与某些社会记忆互相之间所产生黏离和混淆的感觉。
项目有一部五十分钟的实验影片,这是我与吴建新导演第一次的合作。影片以老馆的搬迁作为背景,从摄影师的视角把标本制作的过程、摄影师个人对幼年时光的回忆联系在一起,追求幻境和现实之间某种漂浮感的意境。我希望通过影片展示摄影师的个人身份、记忆与某些社会记忆互相之间所产生黏离和混淆的感觉。 在历经了一年多的拍摄之后,老馆结束了搬迁,新馆在2015年4月开幕。新馆完全不同于老馆,多媒体和新的建筑材料以及大量的触手可及的生物标本,让人目不暇接,为一场实实在在的视觉盛宴。由老馆搬迁过去的旧标本和崭新的标本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大量的多媒体屏幕和部分安装了机械臂的生物模型对于我来说有某种疏离和无法抵抗的震慑力,通过在自然博物馆新址开幕前的少量拍摄中,我们仍旧能够感受到这种强大的控制力在运作着博物馆的转身和崭新的开幕。
在历经了一年多的拍摄之后,老馆结束了搬迁,新馆在2015年4月开幕。新馆完全不同于老馆,多媒体和新的建筑材料以及大量的触手可及的生物标本,让人目不暇接,为一场实实在在的视觉盛宴。由老馆搬迁过去的旧标本和崭新的标本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大量的多媒体屏幕和部分安装了机械臂的生物模型对于我来说有某种疏离和无法抵抗的震慑力,通过在自然博物馆新址开幕前的少量拍摄中,我们仍旧能够感受到这种强大的控制力在运作着博物馆的转身和崭新的开幕。 老馆是我的儿时记忆,上海也是我的家乡。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过去生活的痕迹被不停地抹去,并且带有粗鲁和片段不留的手法,让我经常对于家乡这座城市产生陌生感,记忆无所依托。熟知的场所和儿时的记忆经常被突如其来的新地标和拔地而起的综合性购物娱乐餐饮中心所占据,陌生与不停地被打扰的生活让我无所适从,包括一座自然博物馆。这里应该是在鳞次栉比的水泥建筑中让人安静下来的地方,可以了解生物和生命的由来,感叹自然和造物的神奇,从而对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自然界抱有敬畏之心,更愿意去探索和了解更多关于自然界秘密的地方。
老馆是我的儿时记忆,上海也是我的家乡。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过去生活的痕迹被不停地抹去,并且带有粗鲁和片段不留的手法,让我经常对于家乡这座城市产生陌生感,记忆无所依托。熟知的场所和儿时的记忆经常被突如其来的新地标和拔地而起的综合性购物娱乐餐饮中心所占据,陌生与不停地被打扰的生活让我无所适从,包括一座自然博物馆。这里应该是在鳞次栉比的水泥建筑中让人安静下来的地方,可以了解生物和生命的由来,感叹自然和造物的神奇,从而对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自然界抱有敬畏之心,更愿意去探索和了解更多关于自然界秘密的地方。
本文图片收录于 陆洁《自然的回声》
延伸阅读
上图:上海自然博物馆旧馆正门 陆洁 摄
下图:谈家桢馆长与台湾科学博物馆馆长汉宝德交谈 来源:上海自然博物馆
 它几乎是这座城市数代人的集体记忆,无论你是50后,抑或60后,乃至70后、80后,在所有这些人的童年生活中,他们无一例外地能够回想起自己当年站在这个巨无霸之前战战兢兢的情景。只是此刻我必须将它放过一边,那是因了我们要进入的是1923年,上世纪的20年代。
它几乎是这座城市数代人的集体记忆,无论你是50后,抑或60后,乃至70后、80后,在所有这些人的童年生活中,他们无一例外地能够回想起自己当年站在这个巨无霸之前战战兢兢的情景。只是此刻我必须将它放过一边,那是因了我们要进入的是1923年,上世纪的20年代。 到了1921年的年终,上海金融市场银根紧缩,危机显现,死局初定;而进入次年3月,便是大江东去、落花流水,绝大部分交易所只能在一阵疯狂之后关门大吉,最后剩下的只有六家,六家中的一家便是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
到了1921年的年终,上海金融市场银根紧缩,危机显现,死局初定;而进入次年3月,便是大江东去、落花流水,绝大部分交易所只能在一阵疯狂之后关门大吉,最后剩下的只有六家,六家中的一家便是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 
上海自然博物馆旧馆 来源:上海自然博物馆
作为自然博物馆,它的筹建要在更早一些时候,1956年的12月27日,自然博物馆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确定:馆的性质为“自然历史”,将要筹建并推出的是动物、植物、人类、天文、地质5个专业馆。 在1923年的这个宏伟的大厅内,脚步匆匆、渴望着抓住命运每一个稍纵即逝机会的交易员们,他们中没有人会知道自己的职业将在1937年便宣告终结,同理,他们中也没有人会知道上海自然博物馆将在1958年迁入其间。
在1923年的这个宏伟的大厅内,脚步匆匆、渴望着抓住命运每一个稍纵即逝机会的交易员们,他们中没有人会知道自己的职业将在1937年便宣告终结,同理,他们中也没有人会知道上海自然博物馆将在1958年迁入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