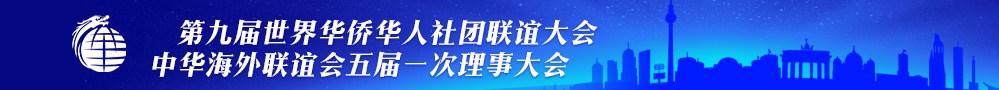萌芽
萌芽 很快,他又作为绘图师入职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并接受了蚀刻版画(etching)相关的训练。他也没停下铅笔和钢笔画的创作,还将部分作品赠与好友约翰·罗斯·基(John Ross Key),其中五幅现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基后来回忆道,不论是在画板上还是随便的一张纸上,只要惠斯勒能找到一处空白,他都会用来画自己中意的人物。
很快,他又作为绘图师入职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并接受了蚀刻版画(etching)相关的训练。他也没停下铅笔和钢笔画的创作,还将部分作品赠与好友约翰·罗斯·基(John Ross Key),其中五幅现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基后来回忆道,不论是在画板上还是随便的一张纸上,只要惠斯勒能找到一处空白,他都会用来画自己中意的人物。

 惠斯勒利用松散的交叉排线(crosshatching)表达纹理和阴影,通过极富活力的潦草线条展现人物姿态——这些方式在他之后的作品经常可见。同时,他巧妙使用铅笔和钢笔打造出深浅不同的灰色和黑色,让人物细节更加生动——从这点已经可以看出他对色彩的运用的研究兴趣。
惠斯勒利用松散的交叉排线(crosshatching)表达纹理和阴影,通过极富活力的潦草线条展现人物姿态——这些方式在他之后的作品经常可见。同时,他巧妙使用铅笔和钢笔打造出深浅不同的灰色和黑色,让人物细节更加生动——从这点已经可以看出他对色彩的运用的研究兴趣。 这幅画记录的叙事性很强,精准地描绘了“波西米亚式生活”极具代表性的一面:年轻男女悠闲聚会,有烟酒相伴,周围摆放的家具极其简陋。和早期的素描作品类似,惠斯勒不知疲倦地使用着交叉排线来构成场景,对女性人物的刻画尤为细腻。站在传统绘画的角度来看,人物和物件之间的空间关系多少有些混乱;但对这位新兴的艺术家而言,这幅画可以说是一次令人满意的实验。不过,惠斯勒很快就放弃了图中这样的圆形格式,开始探索其他艺术理论、风格和技巧。
这幅画记录的叙事性很强,精准地描绘了“波西米亚式生活”极具代表性的一面:年轻男女悠闲聚会,有烟酒相伴,周围摆放的家具极其简陋。和早期的素描作品类似,惠斯勒不知疲倦地使用着交叉排线来构成场景,对女性人物的刻画尤为细腻。站在传统绘画的角度来看,人物和物件之间的空间关系多少有些混乱;但对这位新兴的艺术家而言,这幅画可以说是一次令人满意的实验。不过,惠斯勒很快就放弃了图中这样的圆形格式,开始探索其他艺术理论、风格和技巧。

居斯塔夫·库尔贝在1850年代完成的两幅油画,现藏于巴黎奥赛美术馆。
库尔贝可以说是第一位自觉宣扬和实践现实主义美学的艺术家。他批判法国学院派的古典风格和忠于感性、追求幻想的浪漫主义,执着于以客观的手法展现平民的日常生活和空间的原貌。初来巴黎闯荡的惠斯勒与库贝尔一见如故,被这位老艺术家挑战传统的大胆风格以及使用厚重颜料的方式深深吸引。 往来不断的船只、辛勤的劳动者、不分昼夜运作的烟囱、被灰色雾霾笼罩的伦敦上空.....在这幅油画中,他不加幻想地描述着巴特西——这座工业城市的缩影,力图真实地反映当时平民的日常生活和环境。尽管在选题时秉承着现实主义的信条,惠斯勒的轻盈笔触将他与库贝尔一派的艺术家区分开来;他对瞬息万变的场景的捕捉方式则让人联想起印象派的代表人物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他巧用灰和棕亮色来统一构图的方式,也让当时不少评论家同样耳目一新。有人甚至评价说:“(惠斯勒)有着成为色彩大师的天分和野心。”
往来不断的船只、辛勤的劳动者、不分昼夜运作的烟囱、被灰色雾霾笼罩的伦敦上空.....在这幅油画中,他不加幻想地描述着巴特西——这座工业城市的缩影,力图真实地反映当时平民的日常生活和环境。尽管在选题时秉承着现实主义的信条,惠斯勒的轻盈笔触将他与库贝尔一派的艺术家区分开来;他对瞬息万变的场景的捕捉方式则让人联想起印象派的代表人物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他巧用灰和棕亮色来统一构图的方式,也让当时不少评论家同样耳目一新。有人甚至评价说:“(惠斯勒)有着成为色彩大师的天分和野心。”
克劳德·莫奈,《滑铁卢大桥,灰色天气》,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1865年秋天,惠斯勒前往法国海滨度假胜地特鲁维尔,和库贝尔一同作画。单从这幅《特鲁维尔(灰色和绿色,银色的海)》【Trouville(Grey and Green, the Silver Sea)】就不难看出,这位年轻艺术家已与“现实主义”越走越远;两年后,他甚至会开始抱怨说,库贝尔对他的影响令他厌恶。 相比惠斯勒之前的作品,这幅画较为抽象。他没再想着要真实地还原所见的景色以保证叙事的完整。他仅仅保留了场景内最基本的元素,并有意识地对它们进行平面化处理;画面的立体感更多是通过不同色彩的巧妙融合来打造——这显然有悖于西方传统绘画中的透视法。惠斯勒也不愿再遵从自然的原貌来配色。他更关心色调关系以及颜料和画布本身的特性和相容性。能否刺激感官上的愉悦成为他判断作品好坏的新标准。启发他进行这些尝试的,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风靡欧洲的日本艺术,特别是日本版画。
相比惠斯勒之前的作品,这幅画较为抽象。他没再想着要真实地还原所见的景色以保证叙事的完整。他仅仅保留了场景内最基本的元素,并有意识地对它们进行平面化处理;画面的立体感更多是通过不同色彩的巧妙融合来打造——这显然有悖于西方传统绘画中的透视法。惠斯勒也不愿再遵从自然的原貌来配色。他更关心色调关系以及颜料和画布本身的特性和相容性。能否刺激感官上的愉悦成为他判断作品好坏的新标准。启发他进行这些尝试的,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风靡欧洲的日本艺术,特别是日本版画。
歌川广重所创作的《东海道五十三次》系列之一
惠斯勒对东方美学的迷恋在他进行人物主题的探索时也时常可见。在《艺术家在他的工作室》(The Artist in His Studio)这幅油画中,亚洲元素就十分丰富:中间的女孩身着浅粉色和服,手持一把日本扇子;左边的架子上,艺术家珍爱的瓷器收藏熠熠闪光;墙面的上方还挂着三幅日本卷轴。 惠斯勒喜爱使用轻薄的颜料为画面创造一种通透感。在这幅画中,在白色和浅粉色的服装之下,他为画布所上的基底色清晰可见。
惠斯勒喜爱使用轻薄的颜料为画面创造一种通透感。在这幅画中,在白色和浅粉色的服装之下,他为画布所上的基底色清晰可见。 “夜曲”系列中展出最多的作品之一是这幅《蓝色与金色的夜曲——南安普顿的水面》(Nocturne: Blue and Gold—Southampton Water),于1900年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购入。
“夜曲”系列中展出最多的作品之一是这幅《蓝色与金色的夜曲——南安普顿的水面》(Nocturne: Blue and Gold—Southampton Water),于1900年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购入。
惠斯勒的水彩画,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惠斯勒的蚀刻版画,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惠斯勒的石印画,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惠斯勒在芝加哥的成名主要得益于新闻界的推波助澜。1871年大火之后,芝加哥能涅槃重生、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艺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时,《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报道将惠斯勒带入人们视野,赞誉他为“在海外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艺术家”。当地的评论家和收藏家纷纷相信,这位艺术家有能力为这座城市带来新的生机。1885年,《芝加哥论坛报》再次报道惠斯勒,向公众介绍了他的展览目录《蚀刻版画和针刻法:威尼斯,第二系列》(Etchings & Drypoints: Venice, Second Series)。 这本目录还有个副标题,叫做《惠斯勒先生和他的评论家》(Mr. Whistler and His Critics)。不用怀疑,这是惠斯勒亲自取的。他从过往收到的批评意见中精心挑选出一部分汇编出一个合集,并兴致勃勃地为每一条评论添上注解——当然,都是他的冷嘲热讽,只为挫挫评论家们的锐气。这样的行为在英国人那里只能用“低俗”来形容,到了芝加哥却成了“对文学的好奇心”。当地的民众不再只钦佩惠斯勒对色彩“超群出众”的感知,他桀骜不驯的态度让他这座粗犷的城市备受欢迎。
这本目录还有个副标题,叫做《惠斯勒先生和他的评论家》(Mr. Whistler and His Critics)。不用怀疑,这是惠斯勒亲自取的。他从过往收到的批评意见中精心挑选出一部分汇编出一个合集,并兴致勃勃地为每一条评论添上注解——当然,都是他的冷嘲热讽,只为挫挫评论家们的锐气。这样的行为在英国人那里只能用“低俗”来形容,到了芝加哥却成了“对文学的好奇心”。当地的民众不再只钦佩惠斯勒对色彩“超群出众”的感知,他桀骜不驯的态度让他这座粗犷的城市备受欢迎。 1893年的哥伦布世界博览会总共展出了惠斯勒的6幅油画和50幅版画。如此耀眼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时在世博会担任要职的帕默。
1893年的哥伦布世界博览会总共展出了惠斯勒的6幅油画和50幅版画。如此耀眼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时在世博会担任要职的帕默。
惠斯勒为埃迪所画的肖像,《肉色和棕色的改编曲:阿瑟·杰罗姆·埃迪的肖像》
在1871年大火和世博会之间的二十年里,惠斯勒逐渐成为芝加哥人的宠儿。虽然直至逝世都未曾踏入这座城市,他对这里却有着难解的情愫。他曾对朋友感叹:“芝加哥,天哪,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我真该抽空去看看我的祖父建立起来的城市!我的叔叔还是迪尔伯恩堡(Fort Dearborn)(位于芝加哥的军事要塞,在1871年大火中被毁灭)的最后一任指挥官!”
 千变万化的大海是惠斯勒永恒的灵感来源。19世纪80年代,惠斯勒回归户外作画,用最简单的构图元素营造海岸生活的氛围,一如往常地追求着色彩的和谐。1893年,他来到法国布列塔尼(Brittany)小镇,重新回到大画幅的画布上创作,记录下艳阳之下的迷人海景。
千变万化的大海是惠斯勒永恒的灵感来源。19世纪80年代,惠斯勒回归户外作画,用最简单的构图元素营造海岸生活的氛围,一如往常地追求着色彩的和谐。1893年,他来到法国布列塔尼(Brittany)小镇,重新回到大画幅的画布上创作,记录下艳阳之下的迷人海景。